我和老伴种的梨树被邻居告状,镇长亲自上门看 转身就打了三个电话
那棵梨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。
具体哪一年种的,我也记不太清了。应该是九十年代末,那时候儿子刚考上大学,我和老伴心里高兴,想着种棵果树纪念一下。老伴说,“咱种棵梨树吧,寓意好,’梨’和’离’同音,种了梨树,儿子就不会离开我们了。”
当然,这都是老伴的迷信。儿子大学毕业后,还是去了城里,一年回来不到三次。
梨树倒是老老实实地在我家院子里长大了。春天开白花,秋天结梨子,我和老伴也习惯了每年爬上木梯摘梨的日子。
这棵树挺争气,长得比我家的平房还高。树冠很大,有点像把巨大的绿伞。我家院子不大,树枝长长了,就伸出了院墙,搭到了邻居李大爷家的院子里。
这事本来也没什么。镇上别的邻居之间,谁家的树探出了枝子,也就互相谅解,从来没人计较这个。我们这代人,哪有那么多事儿?
去年八月中旬,老伴刚洗完头发在院子里晾着,身上搭着条毛巾,头发还滴着水。忽然听见院门外有人敲门。
我正在看电视,听见声音,就站起来喊了句:“谁啊?”
院门外传来李大爷的声音:“老杨,是我。”
我们家跟李大爷家处了三十多年邻居,按理说是熟得不能再熟了。可这两年关系有点疏远。主要是李大爷老伴去世后,儿子把他接到城里住了几个月。回来就变了个人似的,整天嫌这嫌那,说我们这镇上太落后,连个像样的购物中心都没有。
我开了院门,李大爷站在外头,手里拿着把老式的蒲扇,脸涨得通红。
“老杨啊,你家那棵梨树怎么回事?枝条都伸到我院子里来了,我在院子里走都绕着走。今天我家小孙子来了,在院子里玩,一头撞到你家的树枝上,眼睛差点戳瞎了。”
我挠挠头:“这么严重?”
李大爷瞪大眼睛:“可不是吗?你得把伸到我院子的枝条都锯掉。”

这事来得突然,我都没反应过来。老伴在院子里听见了,走过来说:“李大爷,这树都二十多年了,树枝伸过去也好些年了,以前怎么没事呢?”
“以前是以前,现在是现在!”李大爷的声音高了起来,“你们要是不处理,我就去镇政府告你们!”
老伴脸一沉:“树又不是故意伸到你家院子的,再说咱们当了一辈子邻居,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?大不了我们把树枝修修?”
“修?全锯掉!”李大爷转身就走,“你们等着镇政府的信吧!”
晚上,老伴坐在院子里,抬头看着那棵梨树,一声不吭。我知道她在想什么。这树是儿子考上大学那年种的,老伴把这树跟儿子联系在一起,对这树有感情。
“要不,我明天去李大爷家好好说说?”我问。
老伴摇摇头:“算了,树枝修一修就是了。”
可第二天我刚要拿家里的锯子修枝,就接到了镇政府打来的电话。负责咱们片区的小林说,李大爷把我们告了,说我们家的树影响他家正常生活,要求我们把树锯掉。我们得去一趟镇政府。
老伴一听就火了:“锯掉?凭什么锯掉?修枝还差不多!”
去镇政府那天,老伴穿得特别整齐,还抹了点口红。我知道她是较着劲儿了。
小林接待了我们,听了事情经过,皱着眉说:“这种事情,还是私下协商比较好。”
他给李大爷打了个电话,请他也来一趟。
李大爷来了,一进门就嚷嚷:“树必须锯掉!那玩意儿长那么高,万一刮大风,树倒了,砸了我家房子怎么办?”
“李大爷,您这就有点过了。”我忍不住说,“那树好好的,怎么会倒?再说咱们村前几年不是有个大风,也没见哪棵树倒了啊。”

“那是运气好!”李大爷瞪着眼睛,“我跟镇上的人都说了,那树太危险,必须处理!”
小林看事情没法协调,就说回头报告给领导。
回家路上,老伴一直没说话。我知道她心里不痛快。
那棵梨树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树下,我和老伴经常摆个小桌子,喝茶,聊天,看着树影婆娑,日子过得挺惬意。夏天,老伴还在树底下放个藤椅,午睡,说树底下凉快。
回家后,我们就开始修剪伸到李大爷院子的树枝。修了一下午,出了一身汗。我爬在梯子上,老伴在下面接树枝。
正干着,听见院外有人喊:“杨大爷!在家吗?”
我从梯子上下来,开了院门,是住在村东头的王婶。
“杨大爷,听说李大爷告你家梨树去了?”
消息传得可真快。
老伴接过话:“可不是嘛,说我们家梨树挡他们家道了,让我们锯掉。”
王婶子摇摇头:“这李大爷,自从去了趟城里,回来就变了个人。”
她压低声音:“你们知道不?前阵子,刘婶子家屋后种了几棵玉米,李大爷也去告了状,说那玉米长太高,挡了他家的阳光。后来刘婶子没办法,只好把玉米割了。”
我和老伴对视一眼,这事真没听说过。
“不行,这树不能锯。”老伴摘下围裙,“咱去找村长评评理。”

村长老周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,做了二十多年村长,在村里很有威信。他听了我们的事,摸着下巴上的胡子茬儿想了想:“这事嘛,按理说,树枝伸到人家院子里,是该修一修。但是让你们把整棵树锯了,那也太过分了。”
他站起来:“走,我去看看那棵树。”
刚走到我家门口,就看见小林骑着摩托车过来了。
“杨大爷,镇长让我来看看这棵树。”小林说。
这下我和老伴都愣住了。这么点小事,怎么惊动镇长了?
小林看出我们的疑惑,解释道:“李大爷可能有点关系,他侄子在镇政府工作,这事惊动了镇长。”
我心里咯噔一下,心想这事怕是难办了。
村长老周拍拍我的肩膀:“没事,咱们实事求是。”
树在过去这个季节结了不少梨子,今年倒是少了点。老伴总说,这树跟人一样,也会有情绪,也会累。
小林看了看树,拍了几张照片,说回去汇报情况。
第二天,镇长郑书记亲自来了。
郑书记大概五十多岁,头发有点花白,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衫,下身是黑色西裤,干净利落。
他看了看那棵梨树,又走到李大爷家去看了看树枝伸过去的情况。
“这树多少年了?”他问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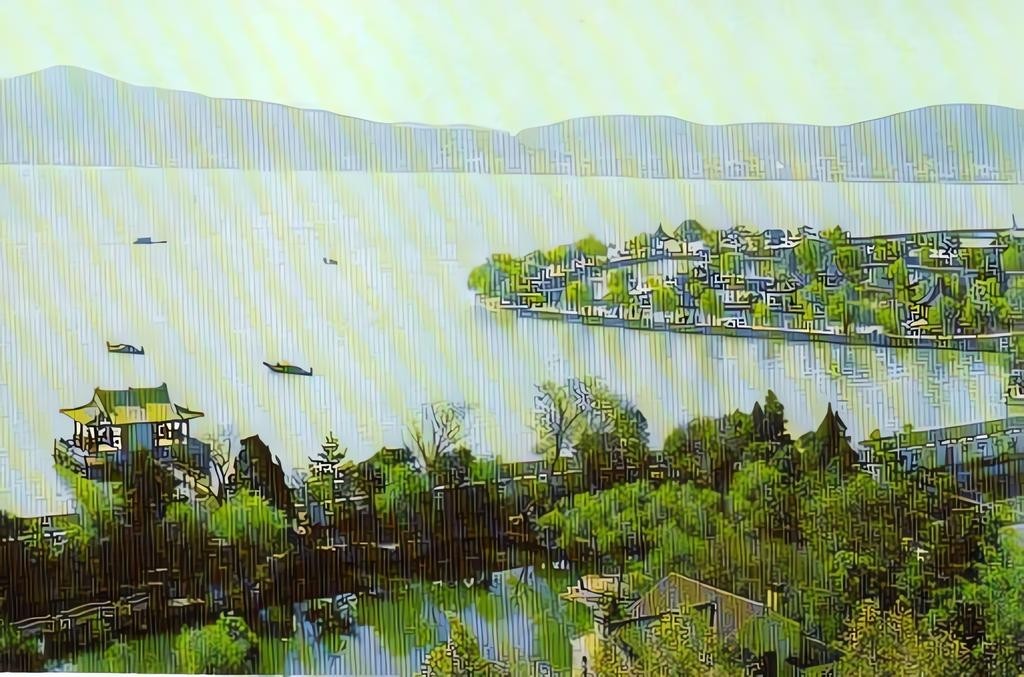
“二十多年了,具体记不清了,反正是儿子考上大学那年种的。”
郑书记点点头,从口袋里掏出烟,递给我一根。我摆摆手:“不抽,早就戒了。”
他笑笑,自己点了一根,吸了一口,抬头看着梨树发呆。烟雾在树叶间升腾,有种说不出的意境。
“树枝伸到李大爷家那边,是该修一修。”郑书记说,“但是把整棵树锯了,那就没必要了。”
我和老伴松了一口气。
郑书记转过身,拿出手机,拨了个号码:“喂,小王啊,你查一下,李家东头那块地是不是咱们镇的规划用地?”
挂了电话后,他又拨了第二个:“老赵,你看一下,咱们镇上关于私人住宅区树木管理有什么规定没有?”
打完第二个电话,他看了看表,又拨了第三个:“小张,你过来一趟,带上咱们规划图。”
郑书记放下电话,对我们说:“你们先把伸到李大爷院子的枝条修掉,其他的等我处理完再说。”
老伴小声问我: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
我摇摇头,也不明白。
一个小时后,郑书记的秘书小张骑着电动车来了,手里拿着一卷图纸。郑书记接过图纸,在我家院子里摊开,仔细看了看,用手指着一个点:“这块地是规划要建幼儿园的,对吧?”
小张点点头:“是的,郑书记。”
郑书记收起图纸,转身对我说:“杨大爷,实不相瞒,李大爷想把他家院子卖了。有个开发商看中了他那块地,想建个小超市。但是按照咱们镇的规划,那一片是不允许开商店的。所以李大爷可能是想借你家的树,找个理由搬走,好卖了那块地。”

我和老伴惊讶地张大了嘴。
“但是呢,”郑书记继续说,“我刚才查了一下,李大爷家那块地其实已经被纳入了镇里的规划用地,准备建幼儿园。只是还没来得及通知他。”
郑书记笑了笑:“这事啊,我来处理。你们把伸到人家院子的树枝修一修就行了,树是不用锯的。”
老伴长出一口气:“谢谢郑书记。”
郑书记摆摆手:“不用谢,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对了,你们这树结的梨好吃吗?”
“可好吃了!”老伴立刻兴奋起来,“又甜又多汁,每年都有不少呢。”
“那今年结了梨,别忘了给我送几个尝尝。”郑书记笑着说。
郑书记走后,我和老伴继续修剪树枝。我爬在梯子上,小心地锯着伸到李大爷院子的枝条。
“这李大爷,真是的。”老伴在下面接着枝条,不住地摇头,“好端端的,图什么呢?”
“人各有志吧。”我说,“可能他想搬到城里去住。”
“城里有什么好的?”老伴撇撇嘴,“楼上楼下的,也没个院子。哪有在咱们这儿自在?”
修剪完树枝,我和老伴坐在树下休息。傍晚的风很凉爽,吹在身上,舒服极了。
“这树,以后可不敢让它长那么放肆了。”老伴说。
我点点头:“是啊,也别让它惹麻烦。”

三天后,李大爷来敲门了。
开门一看,他站在门口,手里拿着个纸袋子,脸色不太好看。
“老杨,这是前几天你们给我家孙子买的糖,我给你们送回来。”他把纸袋子递给我。
我愣了一下,这糖是前些日子李大爷的小孙子来玩,老伴给买的。怎么还回来了?
“李大爷,这是给孩子的,你还回来干什么?”
李大爷抿着嘴唇:“我家要征地了,准备建幼儿园。我们可能要搬走了。”
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。
“其实吧,”李大爷叹了口气,“我这把年纪了,也不想搬。但是我儿子非要我去城里住,说这边条件差。我寻思,要真有个理由搬走,他们也高兴,我也能顺水推舟。”
他搓搓手:“没想到镇上早就规划好了,这下房子肯定保不住了。”
老伴从屋里出来,听见了李大爷的话:“李大爷,你就算搬走了,有空也常回来看看。我们这么多年的邻居了。”
李大爷点点头,眼圈有点红:“我也舍不得这地方。”
他转身要走,又回过头来:“对了,你们家那梨树,到时候结了梨,别忘了给我留几个。我吃了二十多年了,挺想念那个味道的。”
我笑着点头:“一定留着。”
李大爷走后,老伴站在院子里,看着那棵修剪过的梨树,若有所思。

“你说,”她突然问我,“咱们是不是也该去城里住?儿子不是一直让咱们去吗?”
我摇摇头:“我可不想去。城里那房子,连个能踩土的地方都没有。再说了,这梨树怎么办?”
老伴看着树,笑了:“也是,这树挺好的,结的梨也甜。”
第二天一早,村长老周来了,说是镇里要把我家这片划为”古树保护区”,我家那棵梨树被列为保护对象。
“啥?古树?”我惊讶地问,“我家这树才二十多年啊。”
老周笑着说:“郑书记说了,你家这树有历史意义,是咱们镇上最早种的梨树品种之一。以后每年还会给你们一点保护费。”
我和老伴面面相觑,哭笑不得。
这事传开后,村里人都来看我家的”古树”。有人说梨树通人性,知道保护自己;也有人说是郑书记照顾我们。
不管怎样,我家那棵梨树算是保住了。今年它开了特别多的花,估计到秋天,梨子会结得很多。
老伴常在树下坐着,一边择菜一边跟树说话,好像那真是个能听懂人话的老朋友。
有时候我也会想,这棵树见证了我们生活的起起落落,它在,家就还在。树枝可以修剪,但根是不能动的。
就像我们这些老人,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大半辈子,身上多少带着这方水土的味道,哪是说搬就能搬得走的?
昨天,李大爷过来说,征地的事有变动,可能要推迟几年。他表情复杂,好像既失望又松了一口气。
临走时,他看了看我家的梨树,问我:“明年春天,这树开花的时候,记得喊我来看看。”

我点点头,心里明白,李大爷大概还是舍不得离开这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。
有些东西,比如那棵树,比如这片土地,在不知不觉中,已经成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。
老伴昨晚坐在树下,看着月光透过树叶洒在院子里,说了句:“这日子,挺好。”
我想,或许明年春天,我和老伴还会在这树下喝茶,看花开;秋天,我们会继续爬上梯子摘梨;再过几年,当我们爬不动梯子的时候,可能会有孙子帮我们摘。
生活就是这样,人一辈子总会经历很多事,但最终留下的,往往是那些看似普通的日常时光。
当然,那三个神秘的电话到底是什么内容,我们至今也没完全弄明白。不过,郑书记后来来我家吃了一回梨,笑着说:“有些事情,知道得太清楚反而不好。”
也许他是对的。有些谜底,留着更好。
